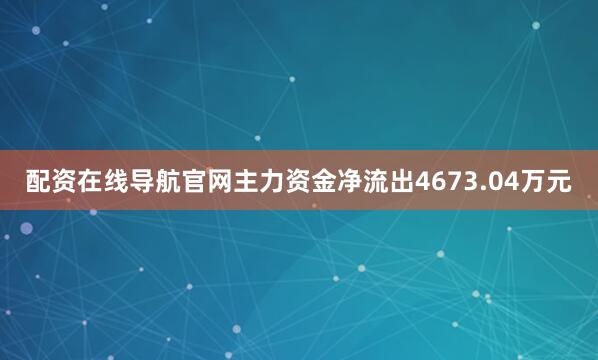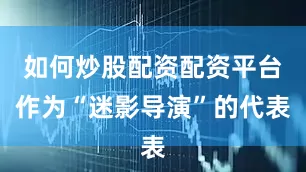
毕赣的《狂野时代》以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姿态横空出世,不仅延续了导演一贯的“诗电影”美学,更以激进的感官实验和时空重构,完成了对电影媒介本质的终极叩问。这部作品如同一座用光影浇筑的迷宫,既承载着电影史的厚重回响,又撕裂了传统叙事的边界,在碎裂的时空碎片中重建了属于电影的狂野乌托邦。
影片以“感官五觉 心灵”六章为骨架,却彻底颠覆了线性叙事的逻辑。从清末鸦片馆的迷醉到新世纪山城的狂欢,毕赣像一位时空采蜜人,将历史断层中的边角废料(失聪者的默片世界、风雪山寺的苦痛禅意、车站特异功能的超现实)淬炼成跳跃的蒙太奇诗篇。这种“报纸边角奇闻”式的叙事策略,实则暗含对电影本质的隐喻——电影本就是从现实缝隙中偷渡来的幻想碎片。
展开剩余81%毕赣的野心在于将类型电影化为感官实验的容器:默片章节的肢体喜剧、谍战戏码的紧张节奏、奇幻史诗的视觉奇观……类型元素不再是故事的外衣,而是被拆解为纯粹的感官刺激单位。当科幻设定(同一人物的时空穿越)成为黏合剂,观众恍然发现,所有类型不过是通向“电影性”本质的路径标记。
毕赣在《狂野时代》中践行的“感官暴政”,是对电影作为综合艺术的极限挑战。他强迫观众用眼睛品尝味道(如风雪山寺中“痛感”与“苦涩”在口腔中的视觉化呈现)、用耳朵触摸质地(鲜血滴落声化作镜面碎裂的波纹)、用鼻腔看见记忆(烧焦扑克牌的气味勾连时空)。这种通感实验远超一般修辞,而是将观影体验推向知觉混乱的临界点——当视觉暂退,听觉成为主角;当触觉侵袭味觉,身体便成为银幕本身。
更危险的是,毕赣将“疼痛”升格为电影的核心语法。无论是牙齿撞击石头的生理痛楚,还是重生时震颤的灵魂刺痛,疼痛在此不再是情节道具,而是唤醒观众感官的武器。这种对“痛感”的痴迷,恰似电影诞生之初卢米埃尔兄弟用火车进站制造的眩晕——毕赣试图用现代电影技术重现那种原始的、生理性的观影震撼。
作为“迷影导演”的代表,毕赣在片中完成了对电影史的仪式性朝圣:从卢米埃尔的现实主义冲动,到梅里爱星际旅行的造梦魔法,再到威尔斯“篡改现实”的预言野心。但不同于简单的致敬,他将这些经典碎片投入自创的时空熔炉,让卡努特大帝的蒸汽船与山城巷弄的摩托车共舞,让默片时代的追逐戏与5G时代的特异功能者对话。这种“暴力剪辑”并非解构经典,而是以平等目光重塑电影史——所有伟大创作都不过是“幻想与爱”的不同变奏。
诗歌在影片中的蜕变尤为惊艳。前作中作为装饰的诗句(如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的苹果隐喻)此刻已渗透骨髓:眼睛成为“放映机/投影仪”的悖论共生,失聪者化作“镜面”通往平行时空。毕赣的诗不再需要外部阐释,而是直接成为影像的呼吸节奏。当诗句从字幕解放,化为镜头运动、光影震颤时,电影终于实现了对文学性的反噬。
24岁的易烊千玺以“迷魂者”身份穿梭于时空裂缝,这个角色堪称毕赣电影宇宙的关键密码。他既是故事中的梦境穿梭者,也是现实中的观众代言人——我们何尝不是跟着这个少年,在不同时空的碎片中寻找电影的魂魄?易烊千玺的表演摒弃了偶像包袱,以近乎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感游走于各个篇章,其空洞的眼神恰似银幕本身:既映射欲望,又保持疏离。
舒淇的回归则构成另一重隐喻。从《刺客聂隐娘》的古典隐忍到本作中车站奇女子的癫狂生命力,她的存在像是对华语电影女性形象的隔空对话。当两人在逼仄巷弄中共舞,历史与当下、东方与西方、经典与先锋在此刻达成奇妙和解。
《狂野时代》最深层的野心,是在一个数字娱乐统治的时代,为电影正名。当短视频蚕食注意力、AI取代创作时,毕赣用两个半小时的“短暂一瞬”证明:电影仍能通过感官轰炸唤醒肉身,通过虚构故事触碰真实。那些风雪山寺的苦修者、镜馆里的失聪者,何尝不是当代人的隐喻?而电影,正是让他们在黑暗中重逢的宗教。
戛纳的掌声不仅是对毕赣天才的认证,更是对电影这一古老媒介生命力的集体投票。在这个意义上,《狂野时代》不只是一部电影,更是一封写给未来电影院的情书——只要人类仍需幻想与爱,电影的狂野便永不会终结。
发布于:江西省查查看股票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